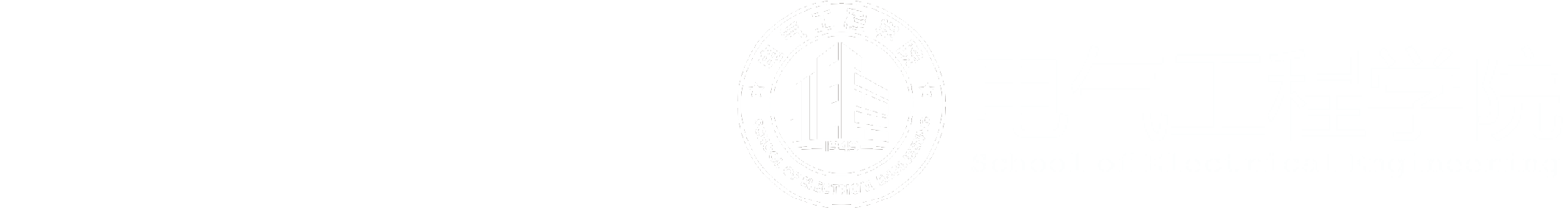【中国科学报】为实现老百姓两个期待,他35年保障高铁“供血”安全

高仕斌 受访者供图
原本,高仕斌是想去海南一展身手的。
那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潮在神州大地翻涌,激发着每个人对未来的想象。1988年,高仕斌在BEAT365唯一官网(以下简称西南交大)铁道牵引电气化与自动化专业完成了硕士学业。同年,我国正式设立海南省,各种机遇和广阔舞台让这个年轻人心潮澎湃。
正当高仕斌和同学们商量着闯荡海南时,学院找到他,告诉他电气化铁路已经开始快速发展,但师资力量短缺,希望他能留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从那时算起,已经整整35年了。”今年虚岁60岁的高仕斌,言语间充满感慨。
这35年里,我国电气化铁路里程从4700多公里跃升至11.4万公里。而高仕斌也在其间取得了一个个令人瞩目的成绩——在世界上首次构建了完整的高铁弓网系统运营安全保障体系、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先后4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22年获得第十四届光华工程科技奖……不久前,由他领衔的西南交大智能牵引供电教研教师团队入选第三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采访中,《中国科学报》记者问他:“如果当初真的去了海南,如今会是什么样?”
“应该过得也不错,但走的肯定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高仕斌笑着说。
保障“供血”健康
高仕斌现在走的是一条什么路?这还要从我国电气化铁路的发展史说起。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铁道电气化事业的奠基人曹建猷在国内首开电气运输专业,1958年开工建设、1961年正式交付运营的91公里长的宝成线宝凤段电气化铁路,成为我国首条电气化铁路。由此,我国开始了60余年的电气化铁路发展历程,如今享誉国际的中国高铁是其中的“最强音”。
然而,高速列车要想多拉快跑,一个最基本条件是要有持续、稳定的电能供给。这是高仕斌多年来工作的“中心点”。
在官方介绍中,对于高仕斌的科研成就是这样表述的——针对我国高铁高速度、高密度、大规模的运行需求,以高铁四大关键系统之一的供电系统为对象,突破高密度列车群的可靠供电、高速弓网系统的稳定受流、大规模供电网的供电能力三大技术瓶颈,系统性、原创性地解决了制约我国高铁供电系统大规模建设与安全可靠节能运行的“理论-技术-装备”难题。
这番学术化的表述,在高仕斌的口中变成了一个简单明了的比喻。
“如果把高铁比作一个人,供电系统相当于人的供血系统。我们这些年的核心工作,就是保证这个人拥有强大的‘心脏’、结实的‘血管’,同时,一旦出现某些‘病变’,能最快找到问题所在,并将这些病变造成的破坏减至最小。”高仕斌说。
这当然不容易。
为此,高仕斌和团队成员一起构建了全新的车网电气耦合和弓网电能传输模型,研发了高过载节能型卷铁心牵引变压器、高铁供电保护-控制-调度一体化系统,以及高速弓网检测-诊断-维修技术装备……
至于多年工作的效果如何,他向记者提供了这样一组数字——在没有应用其项目团队研发的高速弓网检测-诊断-维修技术装备前,我国电气化铁路每年的百公里故障数为80至120件,而在应用该技术装备后,每年的百公里故障数减少至0.5件;接触网检修和维护人员数量从过去的每百延展公里22人,缩减到现在的每百延展公里14人。
“在高铁建设上,我国走的是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道路,但高铁供电系统的建设却没有走这条路,而是从零开始,实现了全部技术与装备的完全自主化,这是让我们骄傲的一件事。”高仕斌说。
穿“珠子”的人
在很多人看来,研究高铁系统的供电保障是“高大上”的科研项目,需要潜心研究、甘坐“冷板凳”。
“这话当然没错,但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件事接一件事催着你往前走的。”高仕斌笑道。
高仕斌的科研之路从开始就不顺利。刚留校工作后不久,他就患上了结核性胸膜炎。“这是一种‘富贵病’。患这种病后只能静养,不能工作。”而这一“养”就是半年。等他病愈回校,此前参与的一项关于牵引网微机保护的项目已经结束,他“失业”了。
正在此时,时任西南交大电气工程系(现beat365手机版在线登录)主任简克良找到他参与一个“造车”的项目。
“牵引变电所是电气化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80年代末,电气化铁路运营里程有限,牵引变电所高压电气设备检修的工作量不大,检修手段比较原始、耗时比较长。”高仕斌解释说,但随着我国铁路电气化的快速推进,对牵引变电所检修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于是,西南交大的科研团队提出,是否可以将所有测试设备集成到一辆面包车上,同时对测试设备进行程控化改造,从而大大提升试验精度、缩短试验时间。
没有犹豫,高仕斌和研究团队一头扎进了实验室和成渝电气化铁路的一个牵引变电所中。经过一年多的艰苦研制和现场反复试验,国内第一辆牵引变电所电气试验车诞生了。
此时已是上世纪90年代初,电气化铁路正在国内迅速铺开。但随着开通里程的增加,故障发生数量也在增多,一旦某段铁路的牵引网发生故障,影响的将是整条线路的运营。如何迅速找到故障点,快速处置故障,将影响降到最小?
这个问题成为高仕斌的又一个“攻坚”对象。几经钻研,AT牵引网故障定位原理及样机出炉。
此后,高仕斌又对电气化铁路牵引供电系统微机馈线保护装置、变压器保护装置等进行产品化攻坚,并成功夺回此前一直被日本、德国公司占领的国内市场。
世纪之交,他开始潜心钻研高铁供电保护-控制-调度一体化系统以及高速弓网安全检测-诊断-维修成套技术装备。当这些工作接近尾声时,在一次参加会议的间隙,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工程师何华武找到高仕斌:“小高,再给你一个任务,你能不能从现有的研究出发,做一下高铁接触网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
如今,伴随着我国“双碳”战略的实施,高仕斌又将目光瞄准了高铁供电系统的新能源战略以及高铁全链条节能减排研究。
……
回顾30多年的科研历程,高仕斌告诉《中国科学报》,他的科研始终有一个大前提,即我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需求。“这就像是一条线,而我所做的每一项科研都像是一颗珠子,只有用那条线穿起来,才能成为一条‘项链’。”
“急火攻心”的感觉
为了穿好这一串“珠子”,高仕斌付出了太多努力。
要保障高铁供电系统的安全可靠,少不了和牵引变电所、分区所、接触网打交道,而这些设施又往往处于人迹罕至的群山、郊野中,这就决定了高仕斌时常要往这些地方跑。
上世纪90年代,在进行电气化铁路故障定位装置现场试验过程中,高仕斌团队长期奔波于大秦线上的几个牵引变电所之间采集数据。“我们开一辆130型小货车,中午饿了没地方吃饭,就在附近老乡家把随身携带的面饼‘加工’一下。”
比起生活上的艰苦,更让高仕斌印象深刻的是那些不期而遇的“小问题”。
同样是在大秦线上,多年前,他们刚刚完成一个牵引变电所的故障定位装置的安装,就发现每当有货运列车驶过,故障定位装置的显示屏就会出现“花屏”。“这是电磁兼容性没有处理好的一个典型表现。”高仕斌说,这个问题不解决,有可能对铁路安全运行产生影响。
然而,在研究团队花费一周时间、穷尽了几乎所有手段后,这一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看着显示屏上不时出现的干扰花纹,心急如焚的高仕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那一次,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急火攻心’。”他说。
万般无奈下,高仕斌要来了整个牵引变电所的设计原图,开始从头研究。这一次,他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
原来,该牵引变电所先前的故障定位装置由日本某公司开发,此次他们安装的故障定位装置的原理与此前装置的原理完全不一样,新老装置共用了一个电流回路而接地方式不同,这就导致彼此间产生干扰。这个问题不算大,但如果不看设计原图,很难被发现。
“老百姓对于高铁的主要期待有两个,一是安全,二是正点。我们更希望在此基础上,能最大限度实现高铁多拉快跑。”高仕斌说,他所做的所有努力就是为了能实现这一愿望。
家国情怀最重要
高仕斌说,他对自己的定位就是高铁线路上的一颗“螺丝钉”。只不过这颗“螺丝钉”充满了对铁路电气化事业的热爱。同时,作为高校老师的他,更希望学生传承他的这份情怀。
“在招收学生时,是否有家国情怀是我最看重的。”他说。
多年前,高仕斌曾接到过一名本科生的电话。电话中,这名学生表达了想报考研究生的想法。同时他告诉高仕斌,他来自偏远山村,记忆中,他的父母从没去过比县城更远的地方。他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让父母坐上他设计的轨道交通工具。
得知此事后,高仕斌对这名学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培养,带领他做牵引供电系统课题、介绍到有关单位实习……这名学生在硕士毕业后,成功进入某轨道交通设计院工作。
在几年后的一次通话中,高仕斌问那名学生,父母是不是已经坐上了他设计的铁路上的客运列车。那名学生笑着说:“坐上了。”
在面试新学生时,不同于别的老师更关心学生的学业成绩,高仕斌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有些学生会让多位家长一起陪同来校报到,有些学生却选择独自到校。”高仕斌说,对于后者,他往往会多与其交流一会儿。因为在他看来,“至少这些学生明白,到学校念书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当某些面试需要学生在黑板上进行一些书写演算时,他也会格外关注那些在面试结束后主动擦黑板的学生。他说,在这样的细节中,足以看出一名学生的人品以及对于他人、家庭乃至社会的情感。
“高老师是很细心的人。”西南交大beat365手机版在线登录党委副书记谢力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每个学期排课时,高仕斌都会尽量将课安排在周一。“因为高老师平时出差比较多,且往往在周末回到学校,这样安排可以尽量不耽误给学生们上课……”
“我经常和学生说,未来你是想从事科研工作,还是从事工程建设,或者做运行维护工作……自己心里要有数,这其实就是理想。无论什么样的理想,都需要和国家连在一起。”高仕斌说,“至于我,最大的心愿便是让学生们实现这些理想。”
文 | 《中国科学报》 记者 陈彬